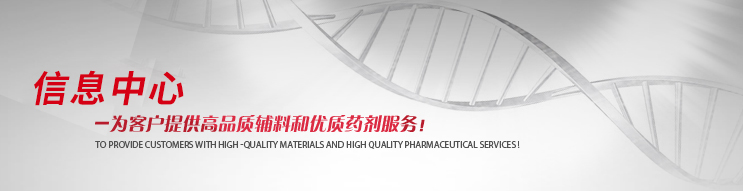AVT:病毒,不单单是“祸害”
文章来源:发布时间:2018-01-23浏览次数: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他是中国分子病毒学的奠基人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创者之一。病毒,这个人类与之争斗又共存的小东西,究竟有什么特性?防治病毒为什么这么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能否利用病毒为我所用?日前,我国首个P4实验室——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完全具备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资质,这让我们又增添了驾驭病毒的利器。
小个头的寄生物
人类认识病毒的历史并不长,仅有120余年。“个头小”是人类对病毒的第一个直观认识。1892年,俄国生物学家伊凡诺夫斯基发现:造成烟草花叶病的病原能够透过细菌滤器。1898年,荷兰生物学家拜耶林克验证了伊凡诺夫斯基的发现,并首次明确了病毒的存在:一类比细菌个头小,能使植物得病(如烟草花叶病)的传染病原。同一年,德国生物学家莱夫勒发现病毒也可以引起动物发病。此后,科学家们又鉴定出感染人类、昆虫甚至细菌的病毒,而这些病毒都是“小个头”。现在,借助电子显微镜,科学家早已能够直接观察形形色色的病毒:它们绝大多数的大小只有20纳米~200纳米,相当于鸡蛋的一百万分之一,细菌的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病毒不仅个头小,结构也相对简单,一般由蛋白质衣壳包裹核酸遗传物质(DNA或RNA)组成,有的在衣壳外还会套上“一件脂蛋白面料的囊膜外套”。
虽然病毒可以感染几乎所有的细菌和动植物,但它们却算不上完整的生命体——它们自己没有独立的代谢和能量转化系统,必须靠感染寄生在其他生命体的活细胞中,借助细胞的结构、“原料”、能量与酶系统生活。
基于病毒具有彻底的寄生性,科学家们判断病毒的起源要晚于细胞;又由于病毒和细胞的遗传物质在表达调控和序列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科学家们推测病毒可能是由细胞或细胞组分演化而来。
经过亿万年的进化,自然界产生了林林总总的病毒。虽然它们看上去形态各异,但是科学家们还是给它们排了个队。最经典的分类方法由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科学家戴维·巴尔的摩建立,其分类依据是不同病毒遗传物质不同、产生信使RNA(mRNA)的方式不同。这种分类方法既找准了病毒生命周期中必经的关键环节,而且也非常简洁,数千种病毒被分为7类:双链DNA病毒、单链DNA病毒、双链RNA病毒、正义单链RNA病毒、反义单链RNA病毒、单链RNA反转录病毒和双链DNA反转录病毒。
防治病毒难在哪里
防治病毒难,首先难在病毒的差异性很强,即便同一类病毒也有很大差异、致病能力也大相径庭。双链DNA病毒中的成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痘病毒科病毒属于双链DNA病毒,这一科的病毒中有个大名鼎鼎的成员——天花病毒。天花病毒能导致烈性疾病、甚至致死,历史上曾有数亿人死于天花病毒感染。值得庆幸的是,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已于1979年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毒。
腺病毒科的病毒也属于双链DNA病毒,但是这一科病毒的致病力就要比天花病毒差多了。冬春季节易爆发的腺病毒会造成呼吸道、消化道等黏膜部位的感染,一般出现急性发热、咽喉疼痛、结膜炎、腹泻等症状,体质较好的患者症状则非常轻微,能够自愈。
同属双链DNA病毒的还有乳多空病毒科和疱疹病毒科的病毒,这其中的人乳头瘤病毒、EB病毒、卡波西肉瘤病毒分别是导致人类宫颈癌、鼻咽癌和卡波西肉瘤的重要病因。不过,这些病毒感染人体后一般具有自限性或处于静止状态,不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仅有少数感染者可能由于免疫力下降等原因造成持续感染而发病。
其次,病毒又特别容易变异,疫苗和药物需要不断更新换代。病毒结构简单,基因组复制时缺少严格的校对机制,某些病毒在传播过程中还有可能发生重组,所以变异比较常见。变异导致了基因组序列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同一类病毒表现出不同特点,甚至可以使同一种病毒分出高致病力的病毒株和低致病力的病毒株。
正义单链RNA病毒就是一类容易变异的病毒,其中的许多成员与人类的疾病密切相关,例如我国强制免疫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和人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就属此类。此外,多种近年来关注度比较高的病毒也属于正义单链RNA病毒,比如手足口病的传染病原肠道病毒71型、寨卡病毒、非典型肺炎综合征病毒等。这些病毒近年来致病力变强、出现从动物到人类的跨宿主传播风险,也是因为其基因组中影响致病能力和感染宿主能力的关键位点发生了变异。
病毒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发现病毒基因组中与病毒致病能力有关的变异位点,掌握影响病毒致病能力强弱的机制,并密切监视自然界中病毒的变异及进化情况,研发有针对性的疫苗或药物。
改造和利用病毒的尝试
病毒危害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有些病毒促成了生命科学中很多重要规律的发现,历年诺贝尔奖中至少有14项颁给了与病毒有关的研究。由于病毒的组成和结构相对简单、容易操作,科学家们常常先从病毒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进而管窥到自然界的奥秘。比如,霍华德·特明、戴维·巴尔的摩从病毒中发现反转录现象,完善了生命的“中心法则”。又比如,彼特·杜赫提、罗夫·辛格纳吉在研究体内免疫细胞对病毒的识别时,发现了决定器官移植时是否排斥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为免疫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其次,我们也可以利用病毒以毒攻毒。比如,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引起小儿麻痹症的元凶,为了预防这种病毒,要给幼儿吃一种糖丸,而这种糖丸就是一类安全有效的减毒活疫苗——其有效成分就是基因组变异后毒力减弱的病毒株。糖丸疫苗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科学家阿尔伯特·沙滨发明后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全球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
最后,我们也可以改造和利用病毒,攻克其他疾病。病毒基因组上有许多功能强大的遗传元件,利用这些遗传元件,科学家们设计了各式各样的载体,成为实验室里不可或缺的分子生物学工具。我们将病毒基因组中的致病成分删除、替换上外源基因,病毒就变成了运载基因的“小汽车”。今天,这些“小汽车”已经开始应用于临床,治疗某些遗传性疾病和肿瘤。
此外,病毒中有一些成员能选择性地感染并杀死肿瘤细胞。正义单链RNA病毒中的塞尼卡病毒就是一种天然的溶瘤病毒,它们作为生物类抗肿瘤药物在治疗神经内分泌瘤、小细胞肺癌等肿瘤方面潜力巨大。噬菌体是能够感染、杀灭细菌的病毒,利用噬菌体进行细菌污染或感染的防治,可减少抗生素、消毒剂的使用,避免细菌耐药性的发生,也更加绿色环保。
病毒在不断进化,但人类认识、改造病毒的探索也不会止步。我们相信,在科学家、医护工作者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人类对病毒性疾病的防控会越来越得力,改造病毒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转载自光明日报(作者:姜韶东 单位:中国科学院感染与免疫重点实验室)